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10 威廉姆斯之墓(2/5)
我通常会走悬挂于建筑物外面的那道铁制的楼梯——那是房东去楼顶喂鸽子的时候才会用到的。
我会走到二楼,然后用力推开我房间的窗子,把身体变成一根晾衣绳,从楼梯的栏杆,到房间的窗台,晃悠悠地一荡,就滑进去了。
有时候我会忘记事先把鞋子脱下来拿在手里,所以我窗前的那块榻榻米上,总有那么几个乌黑的鞋印。
管他的,退房子的时候再说。
不过我的轻功还是不够好,飞身进房间的时候,总是做不到想象中的悄无声息,因此耳边总免不了划过邻居似有若无的抱怨——是个在齿科技师学校念专业士的男生。
不过眼下,我不需要回去我的小窝,因为这街道洁净并且安宁得没有人气——没有垃圾,没有噪声,只有静静地亮着灯或灭着灯的童话般的房屋——我觉得我不能对此袖手旁观,因此我背靠着路灯柱席地而坐,拉开袋子里啤酒罐的拉环,用力拆开我刚买的“七星”——还好,牛仔裤的口袋里有一个打火机。
我坐在马路的这头,一个红色的自动贩卖机在马路那头,我们温柔地互相对望着,它宽容地看着我粗鲁地把烟蒂抛到一尘不染的地面上,然后再目中无人地点上第二支。
我知道,它理解我在做什么。
它看着我的样子就像是在看一个任性地在一片寂静如死的雪地上留下第一个脚印的孩子。
刚刚来日本的那年,我也曾居住在一个类似的住宅区。
永远忘不了那个下午,一个身穿洁净的制服,表情平和且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拿着一把电锯,耐心地把整条人行道边上的灌木修剪成一个漫长的矩形。
电锯持续的噪声对他就像空气一样自然,灌木们纷纷折腰的时候他脸上的祥和气息也一如既往。
那个时候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惶恐的错觉:为何这个国家的人们如此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地想要清除掉所有尘世生活中本来该有的污垢呢?难不成这么做了以后,就可以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么?——不过终归只是一闪念而已,后来我渐渐地什么都习惯了。
“嗨,你怎么在这儿?”不知过了多久,便利店女孩经过了我的身边,惊讶地看着我。
“下班了?”我做了个邀请的手势,于是她非常开心地坐到了我的身边,撕开自己背包里的一袋零食吃了起来,像是野餐一样,拿起我身边的半罐啤酒,用力地喝了几口——她倒是完全没拿自己当外人。
“你是新搬来的么?”她问我,“住在这一带的中国人,我基本上都在店里见过,除了你。
” “我上个周末才搬来横滨。
”我淡淡地说。
“那你之前在哪里?”她问。
“沼津。
是个港口,听说过吗?” “那里很小吧。
”她惊呼,“你来横滨做什么,打工?念书?还是做生意啊?” “念书,横滨国立大学。
”我捏瘪了手里的啤酒罐。
“好厉害啊。
”她笑靥如花,“那现在离开学还有两个月,你不回家吗?” 我没有回答,她也丝毫没察觉出来自己已经问得过多。
她歪着头看着我说:“如果你不回家,怕是打算在开学前打一打工赚点钱吧,我在横滨有很多朋友,可以介绍工作给你的。
等下你留个电话给我吧。
” “谢谢。
”我心里已经开始厌烦她。
“喂。
”她好奇地看着我,笑容里浮上来一种微妙的迷离,“你抽烟的样子真好看,很man呢。
” 我自然没有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带着她顺理成章地去什么地方过夜。
事实上,这种女孩子我已见过很多次了。
在夜店鬼魅的灯光下面,在熟人陌生人混迹一堂心怀鬼胎的聚会上面——总是会有像她一样的女孩子,突然之间,眼神里就浮上来一种莫名其妙的贪婪、挑逗、甚至是狎昵——她们会用闪烁着珠光或者已经被无数饮料还原成本色的嘴唇贴着我的耳朵,细细的呼吸暖暖地拂着我的耳膜:“你好有型呢。
”或者是:“你真的很man。
”但是如果我真的将错就错地搂过她们亲吻,她们就都尖叫着躲闪开了。
我真的不明白,我身上是有什么东西让人觉得我十分轻浮么? 在我漫不经心地盘算着怎么摆脱便利店女孩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几十米以外的房间里,我一直开着的电脑“叮咚”一声,替我接收了一份母亲的邮件。
我可以在回家以后的深夜看,也可以在天亮之后的次日看,没有区别。
邮件只是要告诉我,父亲说不定快要死了。
越南的战场并没有给父亲身体上留下什么伤痕——当然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并不知道他只不过在战地医院里抬了几天担架。
他身上唯一的伤疤是在日本留下的。
经常,他在家里呼朋引伴地喝酒至微醺,总会对我亮出他的左臂——那上面有道长而且扭曲的疤痕,他笑着——我知道他自认为那笑声很豪爽,他说:“儿子,看看这个,这就是你爸。
”他的意思是说那道死死地扒着他皮肤的蜈蚣是枚勋章,只有勇敢的人才能获得。
他从前线归来,退伍,娶了母亲——据说是经人介绍的,然后他被分配到一个什么工厂的财务科上班,在我们那个北方小城里,开始了一种人人都认为是恰当的生活。
但是有一天——在大家的回忆里面,那一天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可父亲突然对全家人宣布说:他想出去看看世界。
当时很多人都作过非常肮脏的揣度,他们说新婚燕尔,父亲一定是对母亲怀着很深的不满才会作这种荒唐的决定,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不满呢?我可以想象他们是如何邪恶地相视一笑——不过现在我已经走过了年少时那段最激烈的时光,我觉得还是应该原谅生活在故乡那座城里的人们。
他们的恶意也并非出自真正的邪恶,只不过是出于一种对异类的恐惧。
是父亲教我明白这个的。
我和他就是彼此的异类,所以我们不知不觉间,都以彼此为耻。
我是他的耻辱,这个不用他说,这点自知之明,我有。
他是个豁得出去的斗士。
当他确定了自己不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时,他就能一鼓作气地把它摔得粉碎。
他想办法联系到了一个远得不能再远的亲戚,为他寄来了一张珍贵的担保书,他拼命地学日语,他卖掉母亲的钢琴换来了一张单程机票。
然后,他像是逃亡那样奔向了东京成田机场,铁了心地以为,可以衣锦还乡。
他在那里待了六年,六年里母亲办过一次探亲签证去看他,回来以后,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就是我。
后来,很多年以后的后来——其实就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今年春天,我和母亲并肩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母亲突然像是开玩笑般地说了一句:“那时候我们是在伊豆的一个温泉旅馆。
是淡季。
你爸爸说,淡季过去会比较便宜。
我们把拉门打开,就能看见富士山的影子。
”我疑惑地看着她。
她补充了一句:“我的意思是说,我就是在那几天,有了你。
你去过伊豆吗?我觉得并没有川端康成的小说里写得那么美。
”她眼睛里美好的羞赧令我替她觉得无地自容。
好吧,在那段奋斗的岁月里,旅行是奢侈品,我就是奢侈品的账单。
我知道,她被父亲的病情弄得昏了头,不然,怎么样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被两个敌国王子求婚了雪夜暗度
- 当真咬春饼
- 穿书后我有四个霸姐绾山系岭
- 爽文女配她杀疯了(快穿)临西洲
- 咸鱼飞升重关暗度
- 我始乱终弃前任后他们全找上门了倔强海豹
- 仙君有劫黑猫白袜子
- 万古大帝暮雨神天
- 末世对我下手了一把杀猪刀
- 这只龙崽又在碰瓷采采来了
- 他的余温阿宁儿
- 港黑大小姐在线绿宰盛况与一
- 同桌乃是病娇本娇候鸟阳儿
- 偃者道途不问苍生问鬼神
- 江湖人独孤红
- 穿书后我爱上了蹭初恋热度清越流歌
- 失忆后我招惹了前夫萝卜兔子
- 我在阴阳两界反复横跳的那些年半盏茗香
- 海贼之黑暗大将高烧三十六度
- 重生女配之鬼修雅伽莎
- 他从雪中来过期白开水
- 天赋图腾有时有点邪
- 氪金一时爽闲狐
- 荒野挑战撸猫客
- 女配不想死(快穿)缓归矣
- 小翻译讨薪记空菊
- 星星为何无动于衷秋绘
- 怀火音爆弹/月半丁
- 放不下不认路的扛尸人
- 他的漂亮举世无双Klaelvira
- 眼泪酿宴惟
- 新来的助理不对劲紅桃九
- 卡哇伊也是1吗?[娱乐圈]苹果果农
- 卧底后我意外把总裁掰弯了!桃之幺
- 直播时人设崩了夏多罗
- 单恋画格烈冶
- 反派病美人开始养生了斫染
- 六零年代白眼狼摩卡滋味
- 总裁的混血宝贝蓂荚籽
- 戎先生的失恋日记桃白百
- 男神总想退圈卖保险[娱乐圈]翻云袖
- 班长,请留步!天外飞石
- 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不吃姜的胖子
- 假释官的爱情追缉令蜜秋
- 伺机而动重山外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春生李书锦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小星星黄金圣斗士
- 野生妲己上位需要几步?酥薄月
- 星星为何无动于衷秋绘
- 对校草的信息素上瘾了浅无心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图书馆基情实录飞红
- 放不下不认路的扛尸人
- 结婚以后紅桃九
- 六零年代白眼狼摩卡滋味
- 总裁的混血宝贝蓂荚籽
- 夕照斑衣白骨
- 明星猫[娱乐圈]指尖的精灵
- 掰弯自己也不放过你(直播)几树
- 游弋的鱼乌筝
- 是夏日的风和夏日的爱情空梦
- 循规是笙
- 共同幻想ENERYS
- 恶魔总监:亿万独宠小男友浔弦
- 动物爱人魏丛良
- 我在恋爱综艺搅基李思危
- 宠夫成瘾梦呓长歌
- 如何错误地攻略对家[娱乐圈]曲江流
- 撒谎精发芽芽
- 黎明之后冰块儿
- 甜甜娱乐圈涩青梅
- 竹马危机萧二河
- 你叫什么?我叫外卖晒豆酱
- 他的漂亮举世无双Klaelvira
- 全员黑莲花鹿淼淼
- 玄学大佬回到豪门之后沐阳潇潇
- 六零年代白眼狼摩卡滋味
- 明星猫[娱乐圈]指尖的精灵
- 别慌!我罩你!层峦负雪
- 娇妻观察实录云深情浅
- 鱼游入海西言
- 直男室友总想和我贴贴盘欢
- 学长在上流麟
- 暴躁学生会主席怼人姓苏名楼
- 大叔,你好大江流
- 你的虎牙很适合咬我的腺体ABO麦香鸡呢
- 情敌暗恋我寻香踪
- 共同幻想ENERYS
- 天才作家o白野o
- 如何错误地攻略对家[娱乐圈]曲江流
- 流量小生他天天换人设西西fer
- 撒谎精发芽芽
- 我要这百万粉丝有何用宝禾先生
- 误入金主文的迟先生柚子成君
- 八十年代发家史马尼尼
- 喜提祸害舍木氓生
- 明明有颜却偏要靠厨艺青渊在水
- 我的家在东北隐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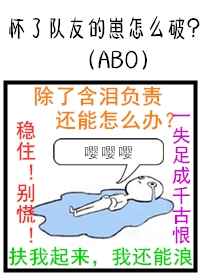




![八十年代之娇花[穿书]](https://www.gotsim.com/img/6224.jpg)